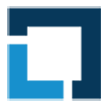“秋宜何处看,试问白云官。”
安于之裹紧身上的被子,窗外的桂花树在秋风的吹拂下摇曳着,摆的幅度不是很大,却能带来满园馨香,只可惜怎么也吹不进这外表华丽内里腐朽的小屋,徒留久居深闺的少女一片灰败的气息。
天上没有云彩,只有湛蓝的天空和不曾被遮盖的大日。窗外,是晴空万里,安于之苦嚼着碗里昨夜残留的药酒,身上的冷意稍减半分。
她的视线投在外头,身体却在里头。她想自己曾在这里待了十三年,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,直至后来舞枪弄剑,策马扬鞭远至塞外,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光。
塞外风景美则美矣,一个少女远行,到底少了些便利。后来的颠沛流离造成了身上难以疗愈的病痛,以至于如今归来,只能靠着喝药苟延残喘几分。
她的嗓音沙哑着,好像吃下了大把的冰雪似的,只是开口,喉咙就痛的眼眶发红。
她抬手测了额温,并不如何烫手,脸颊却泛着微红。她轻笑两声,谁还知道这是曾经肆意潇洒的少年勇士,直到如今这番模样,已经再无力举起刀剑了。
今天,瑟瑟秋风起,她忍不住咳了两声,自嘲地笑笑,怕是呆不下去了吧。
听见门口的仆役传话来,说老爷派人请她过去,她便放下紧抱着的被子,换上一身厚衣,向外走去。打开门的一瞬间,她好像整个人都被风穿透了,冷得刺骨。
几个贴身的丫鬟扶着她上轿,轿辇是很牢固的,纵然并不好看。小厮抬得还算稳当,不到一刻钟,她就到了会客厅。
“父亲。”安于之下轿后向主座的中年人行了个礼。
中年人安邵对她点头,示意她坐过去,到他的座位旁。身边的丫鬟收到命令后,将她搀扶着坐下,静立在一旁。
“这人,你还认识吧?”那位父亲对着会客厅那个跪着的男人说。
“认识。”不卑不亢的声音,声线有一些好听。
“那便好了。”
安于之不知道这两人在说什么,但是听着好像跟她有关,便强忍着喉咙的不适,抬头看向父亲,忍不住询问:“父亲,是在同这位客人说孩儿的婚事吗?”
安于之虽曾远行,但到底与父亲金戈铁马,少了几分女儿娇气,并不遮掩自己打量台下青年的目光。
安邵并没有回答自己重病的女儿,只是沉着脸静静地看着那个跪着的青年,又说:“于之常年生病,生母早逝,又是被宠大的,我本不欲让她嫁人……”
台上人顿了顿,台下人便很上道地开口,对安于之放肆的注视也没有多加言语,他只是依然淡淡开口道:“先夫人与家母定下婚约,定是相信她的为人,亦是相信母亲所教导出的孩儿,于之姑娘与在下亦有儿时情分,只希望再续前缘。此番前来,但凭伯父考验。”
中年人听着这段话,似乎很满意,用手抓起胡子抚摸,忽而大笑。这才对适时咳嗽了两声的安于之说:“于之,这是你母亲为你定下的亲事,先前你病弱,且原家突逢变故,这事便搁置了。现在,既然小覃找来了,你的病也好些了,也是到可以寻亲事的时候了。”
“是,父亲。”安于之压着咳嗽不敢出声,这场景倒是也不用她多说,生母故去,自己体弱,婚姻大事皆有父亲这位将军大人做主,何必她多言,左右是活不长了,嫁谁都一样。
台下人终于被允许起身,坐在安于之一侧的座椅上,目光却并不离开主座上的中年人。
安邵离开了,给年轻人留下了相处空间。
“在下原七覃,家母曾说姑娘长大后的模样也极好看,如今看来,果然如此。”自称原七覃的青年身着白衫,的确是那位勇于直谏惹怒皇帝的原大人家的风格,说话方式也如出一辙,只是稍微有些冷漠了,脸上似乎没有什么表情。
“安于之。”她轻声说道,并不多说,年幼的玩伴不过几年未见,倒也不至于到需要再度开口介绍自己的地步。
十一看书天天乐!充100赠500VIP点券!
立即抢充
(活动时间:10月1日到10月7日)